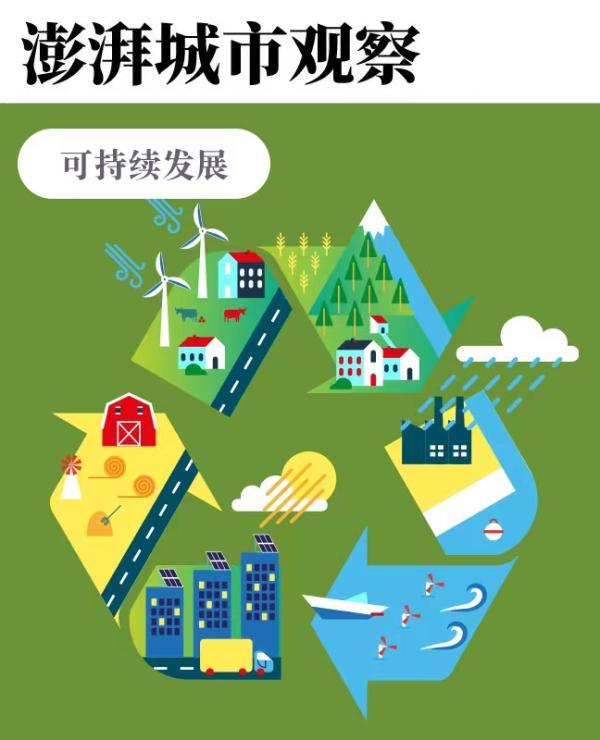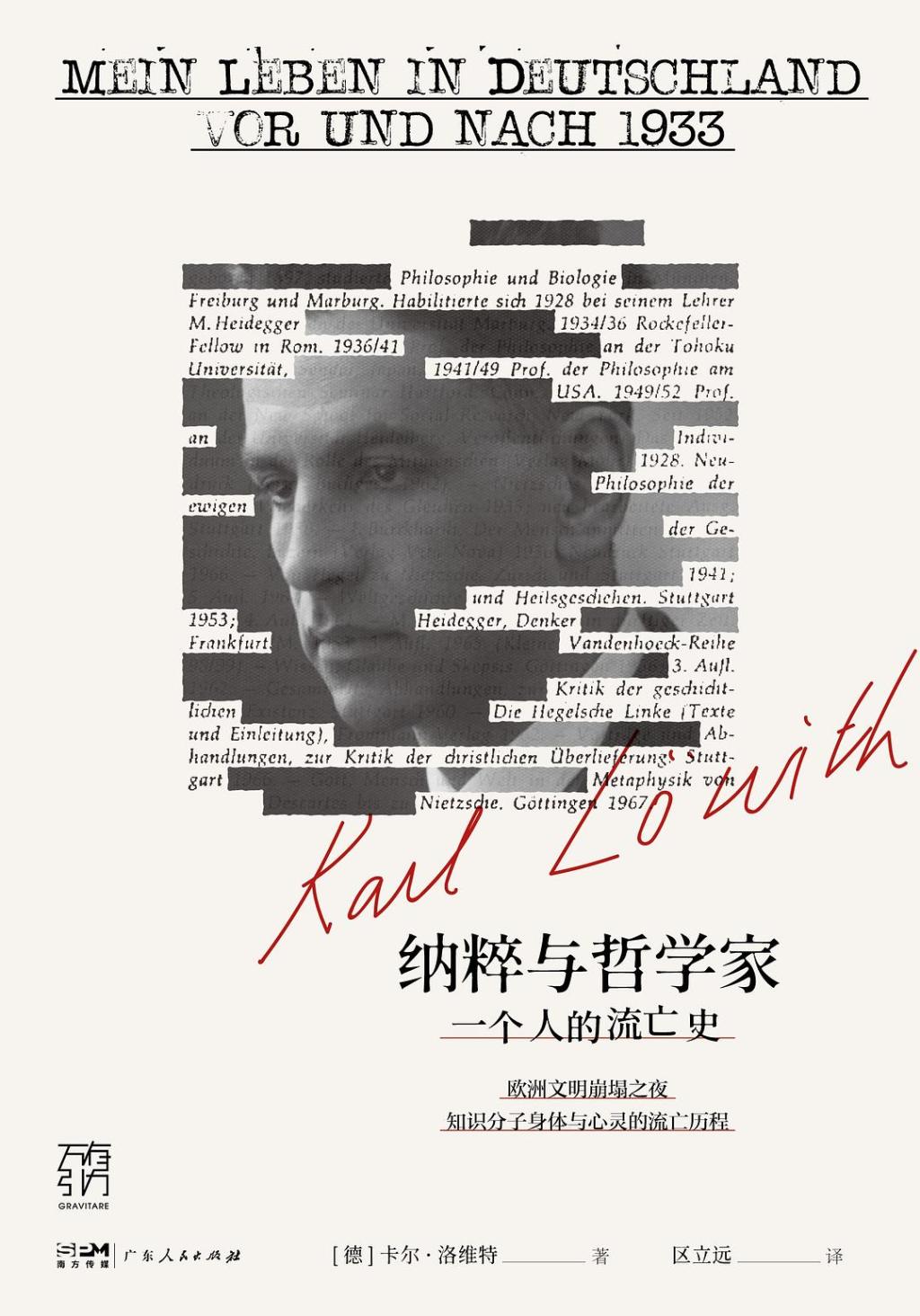
《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德] 卡尔·洛维特著,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5年5月版,316页,78.00元
近日读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的《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6月),先看到的新书推介语就很有吸引力:“欧洲文明崩溃前夜,知识分子身体与心灵的流亡”“《极权主义的起源》亲历版,见证纳粹掌控社会的过程”“当知识分子‘穿上冲锋队队服’,揭示‘纳粹与哲学’的深层纠缠”“纳粹如何利用尼采思想合法化自己的独裁统治,‘一体化’政策如何一步步渗透到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德国大学精神在极权主义下如何崩塌”……我也知道该书就是十几年前我读过的学林版《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那时也在“一周书记”专栏写过一篇很短的书评。现在重读该书中译本的新版本,正好有机会再补充谈一些阅读心得。因此应该先谈谈这部书的前世今生。
洛维特这部写于1940年、出版于1986年的个人回忆与思想录的原书名是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直译是“1933 年前后我的德国生活”。1940年是洛维特夫妇流亡到日本的第四年,埃达·洛维特在该书首版的“补记”中说不记得洛维特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份有奖征文广告,当时他们正计划于次年移居到美国麻州,那里的哈特佛神学院(Theologisches Seminar in Hartford)聘请洛维特去任职。考虑到移居美国之所需,这份颁发奖金的写作计划颇有吸引力。这份以德文书写的征文广告值得重视,其标题是:“一千美金征文广告给所有在希特勒上台前后熟知德国的人!”,下面说明征文的目的是供研究纳粹对德国社会与民族所造成的社会与心理影响所使用,征文的题目就是《1933年1月30日之前与之后我在德国的生活》。因此,洛维特这部书的原书名就是由征文广告所决定的。评委会要求作者简单、直接、完整地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真实发生的事件,评委的兴趣不在于对过去的哲学思考,而是对个人经历的报道,如能引用书信、日记等私人资料则更有可信度和完整性。“就算您从前从未写作过,只要您有好的记忆力、锐利的观察力,拥有对人与人性的了解,您就应该勇敢参加。”这份征文广告还要求字数不短于两万字,截稿日期是1940年4月1日。洛维特在平日就有把想法、与人交往以及每日的事件翔实记录下来的习惯,也很喜欢附上适当的照片、明信片或剪报等图片,因此很快完成写作,在截止期限之前把书稿寄出。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被选用,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直到1973年洛维特去世之后洛维特夫人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才重新发现这部手稿,终于在1986年出版。
因此哈佛大学的这个征文活动是洛维特这本回忆录的前世起因,这事有着特别的意义:美国学术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多就如此敏锐地意识到通过纳粹德国的流亡者的亲历叙事研究德国的重要意义。美因茨大学教授德特勒夫·加茨(Detlev Garz)于1994年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馆里重新发现了这批应征稿件,所以现在知道当初共有两百七十份报告参加应征,文章长度介于一百二十至三百页的打字稿之间。其中有些精彩的报告也已经出版。(译者导言:关于洛维特与这部自传,15页)
该书第一个中译本就是《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根据德国J.B.metzler出版社1986年版单行本译出。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这本《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是同一译者根据同一德文版译出,匆匆对照了一下,新译版本在一些文字上有修订。如果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这个书名当然符合原书和原来的征文题目;但是从今天的阅读与传播需求来看,《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则显然更有吸引力,而且也更突出了书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作为哲学家的作者所思考的核心主题的确是纳粹与哲学家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也正是当年投稿没有被选出的原因,因为在征文广告中已经说了评委的兴趣不在于对过去的哲学思考。
学林版的《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2008年)收入了德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克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为该书撰写的“编者前言”,克泽勒克强调这不是一部事过境迁的往事追忆录,而是一份流亡日本时期所写下的中途报告。“这份文献征引了许多书信,也附上一些与国社党的独裁统治相关的印刷资料。洛维特带着警觉的好奇心与压抑着的愤怒,以及对国社党逐渐转强的鄙视心情,搜集了这些资料。洛维特的亲身经历在这份文献里处处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这也就是此书具有无以复加的现场感的原因。”在他看来,该书有两种切入方式,描绘了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洛维特以1933年的巨变当作叙事聚焦的核心,报道了他在之前与之后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他也深入思索这些经历、思索当前的历史发展带给他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改变了他的人生,并强迫他作出回应。”(《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编者前言”)应该说第二方面的思索更重要的是以存在哲学、现象学的思考为内在核心,是把“当下”与“历史”的存在性与时代的关系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应该时刻想到的是作者写下这些回忆与思考的那种现实语境:距离发生巨大历史转折的1933年只是七年的时间,直至写作之时仍然身处这一历史巨变所造成的个人危厄情境之中,亲身经历中的许多人与事仍然在生活中产生影响——只要我们注意到书中有不少人名是以缩写字母来书写的,就不难体验到一种深切的警惕与忧虑氛围。这也就是克泽勒克所讲的那种现场感,而不是事后之见成为这部回忆录的基本底色。毫无疑问的是,该书的写作本身就是应对双重压力——流亡中的生存压力与因社会巨变而产生的精神压力——的产物,因此它充满了现场感、见证感和思想的敏锐性。可以说,这种短时段之中的亲历叙事在类似洛维特这样的德国著名哲学家的著述中是很少见、很珍贵的,具有相当独特的意义与精神品格。
洛维特自己对这本自传式思想文稿的性质和意义当然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该书完全只是根据自身经历的回忆以及一些书信和从1933年起开始收存的其他第一手文件写出,这些文件既有残缺也带有偶然性。“不过,这份记录的优点也正在于,它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件,它所传达的,不多也不少,正是一幅平凡的景象:一个不涉政治的个人,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真实遭遇的事情——这份记录只有一点不符合实情,那就是语气;人的回忆具有一种力量,即便最痛苦的往事也能加以转化。一个人隔了六年再来叙述,那些往事早已走进了他的人生,成为一种收获,而原先遭受损失时所经历的痛苦,因此也镇静了下来,被掩盖过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经历本身仍然历历在目,足以让我以一种方式描绘那些事件中的人物,使人明白:他们跟我们仍然息息相关,而其程度更胜于我们所希望。有些评判下得严厉,但我无意改得缓和些,因为这些都是新近的往事。”(引言,1-2页)
哈佛大学的征文广告所给出题目明确规定了“1933年1月30日之前与之后”这个时间段,首先促发了洛维特关于“前”与“后”的思考。因此该书“引言”一开头就是由“前”与“后”来切入:“从一战中诞生的独裁政权,跟从前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正开启整部历史的新纪元。而事实上,不可否认地,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化已成事实,这在德国没有人能争辩。而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党人跟那些注定只能缄默的反对者,意见是一致的——正如一位朋友前些日子从德国的来信上所说:‘一切都过去了。’”(1页)我们曾经和一直以来也都对类似“……前”“……后”这样的时间修饰语非常熟悉,而对于“一切都过去了”更是心有所思所感,这也正是阅读洛维特这部回忆录的时候一直萦绕于心的时间叙事。但是在洛维特心目中的“前”与“后”并不是辉格历史观的时间叙事,而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时间开始了”。从观念系谱来说,来自尼采的思想。洛维特在1923年以关于尼采的研究论文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在布拉格的哲学家会议上(1934)提出要把尼采视为“时代的哲学家”,把尼采对于德国的意义放在“革命前”与“革命后” 之间的鸿沟之上来理解,由此来理解德国的演变。(15页)
对于作者和无数德国人来说,1933年都是一个巨大的创伤切口,一个掉进深渊的转折点。在六年之后作者描绘了从个人生活的变化折现出来的历史巨变的阴影及其发展逻辑。书中以大量的生活细节、人与事的交往精准地记录了在一体化运动来临之际知识分子的“观望、被动、苟且、逢迎,以及学生的激进与肤浅,……整个大学体系毫无抵抗,怯懦地接受一体化运动……”(译者导言,6页),记录了德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巨人面前弃械投降”的前兆与进程。
关于纳粹推行的“一体化”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洛维特的亲身体验是非常微观和非常敏锐的。比如关于“前线条款”,一个犹太人必须用参战的经历来换取免受剥夺普通公民资格的“优待”,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荣誉而是一种耻辱。但是旁人对他的这一看法却完全无法理解,于是他马上想到这个人“是这么理所当然地让自己被‘一体化’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他根本毫无知觉。而他的这种无法理解,直到今天仍然使我震惊,因为这说明了一件事:即便是跟他们这些自以为对纳粹的宣传保持冷漠与超脱的人沟通起来,也是如此令人绝望。”(29页)这些人对于犹太人普遍遭受的悲惨命运采取了完全无所谓的态度,竟然毫无顾虑地同意只有纳粹政府所临时规定予以优待的那些人才可以不受迫害,实际上就是以“前线条款”来平抚自己良心的不安——你看,我们的政府还是有人情味的!直到后来纳粹连这一条款都废除了才让他感到生气。在洛维特身边有不少这种人,他们并非心性凶狠的纳粹,但是他们不知为什么能够把不义、罪恶的底线升得那么高,完全超出了普遍人性所能忍受的程度。这是所有“一体化”社会对人性的最大扭曲,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甚至在直到今天的种族政治、战争行动中仍然延续下来。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洛维特以羞耻之心回想起 1933 年抵制犹太商店的那些日子里,马尔堡的犹太商店橱窗上挂着店主的“铁十字勋章”——这是向马尔堡市民充满苦楚的诉求,也是马尔堡的市民之耻。这时候他说:“今天,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毫不迟疑地站在德国的敌军这一边,为他们提供军事与政治上的支援。因为这个德国已是一切人性之敌,也因为这个德国坚决地否决了让我们的生活有价值的一切。如今卷入战争的德国人,他们任何的困境与死亡,都不能使我对这套体系产生的结果感到同情,因为这套体系根本毫无同情之心,而且正狠狠地践踏着人类的尊严。”(31页)
洛维特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深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影响和感染,他说“在德国只有一个人凭借着他的洞见与人格,还能说出意义重大的、使我们感受到号召的话,他就是韦伯。”他和一群学生请求韦伯于1918/1919年冬季学期在他的演讲厅里作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讲,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震撼。“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着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38-39页)韦伯预计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繁花盛开的春天,而是一个幽暗到不可穿透的黑夜。他说在这个已经祛魅的世界上,继续等待先知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行动是没有用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动手去做我们的工作、做好“当前的要求”——当前的要求总是简单而平实的。对于当时的洛维特来说,他的“当前的要求”就是完成学业,不被政党之间的争斗所干扰。应该说,1933年之前的洛维特对于政治斗争的确不感兴趣,他说1918年托马斯·曼发表的一篇《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给他提供了某种程度合理的立场。(40页)
作为一名大学“青椒”,1933年之前的洛维特过得挺顺的:1928年完成就职论文,在马尔堡大学取得“编外讲师”的身份,1929年与柏林女孩埃达(Ada)结婚,1931年得到固定教职,可以妥妥地过上哲学教授的职业生涯。但是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一切都被改变了,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在纳粹帝国语境中这种“就因为……”看起来很无理、很残酷也很自然,因为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之一就是反犹主义,但是这种理由话语却不是独此一家,经过各种话术包装的“就因为”史不绝书,荼毒生灵。接下来就是对犹太人的残暴迫害,对民主原则、自由精神、人格尊严等所有普世价值的公然践踏。洛维特坚信如果韦伯能活到 1933 年,“这场令全德国的大学教授蒙羞的一体化运动,一定动摇不了他,而且情势再怎么极端也是一样。广大胆怯、懦弱、冷漠的同事们,一定会发现他是一个不留情面的反对者。他的言论也或许能够扭转德国知识分子可悲的命运:这命运是知识分子(Intelligenz)自己招来的……他一定会不计任何代价,反对对犹太同事的污名化——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喜爱,而是出自高尚英勇的骑士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的正义感。”(39页)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光凭他的言论能够扭转德国知识分子可悲的命运,我们毕竟比1940年的洛维特看过更多、知道更多一些。
著名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1868-1933)在当时德国文坛影响很大,洛维特认为格奥尔格的圈子成为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精神上的开路先锋,为纳粹主义铺好了道路。“不过话说回来,在大战中成长的一代里较为激进的那些人,又有谁不曾为纳粹主义铺过路呢?他们不都确认了旧价值的崩解,也都对当前还存续的一切加以批判吗?”(52页)这是从一战之前就已经出现、一直蔓延到战后的流行思潮:虚无、衰败、绝望,知识分子以各种不同的身份、目标共同推动着毁灭性而不是建设性的行动。直到纳粹党取得了政权,以强迫统一思想为手段,所有的批判性都被纳入统一的纳粹意识形态需求之中,同时提出的规训是停止破坏、建设“新德国”。洛维特说这是一种相反的崩溃——他们称之为“崛起”。(55-56页)这也不是二十世纪上演的第一次国家力量的“崛起”,知识分子为摧毁自己的力量铺路也不是第一次。很典型的事例是在1933年曾经发表抵制信的著名学者斯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在纳粹掌权几年后也完全臣服于专制思想,摇身一变成了纳粹帝国的代表,令洛维特一开始对其前后变化感到难以理解:“这还是同一个人吗?”(223页)接着他分析了对生存之道的依赖、从众心理、缺乏政治上的洞见等等原因。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受迫害的艺术史学者对内心的剖析更为令人动容:“我也无法忍受他们用那种无耻讪笑的姿态在那里撒谎、欺诈、污蔑与损害正义。”(143页)
在这部回忆录中谈得最多的哲学家无疑是引导他进入哲学世界,使他的学院生涯成为可能的导师海德格尔,他在学术上对洛维特有极大的影响。洛维特对海德格尔既心怀感激,同时也对其政治行为和哲学思想猛烈抨击。哈特·克泽勃克指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维特日后出版的《贫瘠时代的思想家》一书中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在本书的自传叙述中也已经略具雏形。洛维特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无疑十分肯定,但却又坚决地与他保持一种距离,把这两种态度连起来看,就构成一个难解的谜。这个谜不能光从心理学、社会学或哲学的角度来破解,因为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看,总会有一个角落是看不到的。洛维特明亮的眼光穿透每个角落,他对海德格尔诚实地怀着感谢,但又不受这份感谢误导。”(《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编者前言”,3-4页)在“海德格尔的人格”这一小节中,洛维特对他的“人格侧写”是只有最熟悉他的学生才能写出来的:他身穿的介于市民的常服与纳粹冲锋队制服之间的衣着,他的很难描述的面容与总是不坦然的目光,自然流露的表情则是谨慎、狡狯且猜疑的,他讲课的时候只是看着稿子不停地说话,完全不考虑听众。他在生活中将自己封闭起来,遁逃到工作之中使他的本性变得刚硬与僵冷。
在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有两个议题很值得思考。一是海德格尔作为哲学老师所获得的超乎寻常的成功、他的难以理解的著作产生不寻常的巨大影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洛维特提供了他个人的视角和感悟:“起初,他之所以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是因为我们期待他会提出一套崭新的哲学系统,而是因为他的哲学意志所具有的内容的不确定性与纯粹的召唤性,以及他智性之强度与对于那‘唯一的要务’之专注。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个‘唯一’其实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一个纯然的决心,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个面对着虚无的赤裸裸的决心,将虚无主义甚至‘纳粹主义’隐藏在内。然而这决心一开始却也带有一些特征,使人以为它带有宗教意味的忧虑,因而将它的虚无主义与‘纳粹主义’掩盖了起来——事实上海德格尔当时也尚未能坚决地从他的神学源头脱离出来。”(66页)决绝的意志、专注的决心以及带有宗教意味的精神光影,这是在虚无中产生的意志影响力和精神感染力。
二是存在于他的存在学说中的政治可能性,这是很复杂、微妙但又是有迹可寻,甚至在洛维特看来是证据确凿的一段认知探险。从认识海德格尔的难度来讲,洛维特说“我们学生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在他个人的悲壮之情(Pathos)与这种概念的热情(Leidenschaft)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联系。最能了解这一点的,大约是天主教神学家如普日瓦拉与罗马诺·瓜尔迪(Romano Guardini),他们比我们更能看穿海德格尔依恃的前提是什么。”(67页)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就更不用说了,但我还是力图在洛维特的解读中思考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党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契合的。洛维特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有一句不曾明讲的箴言讲起:“愿每一个人在自身存在之内坚强。”这是从路德那里来的,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重要之处仅在于‘每个人只做他能做的事’,在于‘每个人自己的能够存在’(Sein-Können),或者在于‘将个人实存地框限在本有的、历史的事实性之内’”。洛维特说他同时将这种“能够”当作“必须”或“命运”,接着引述了海德格尔在1921年给他的一封信上的话:“我只做我非做不可的且必要的事,而且我只做到我所能做的程度。……我之所以工作,是来自我的‘我在’,是来自我精神上的、全然事实性的根源。存在(das Existieren)缘此事实性而爆发着怒火。”(68页)什么意思呢?洛维特把它放置于与日后的事实联系起来的语境中分析:“谁要是把海德格尔日后对希特勒行动之拥护跟这段时期连起来看,就会发现,早在这最初的、对历史性存在的表达方式里,便已经种下了他后来的政治抉择的根源,所欠缺的只不过是接下来的一步:从半宗教意味的孤离状态走出来,然后把‘每个人本有的’此在(Dasein)及其‘非如此不可’,应用到他‘德意志的此在’及其历史的命运上,以便将这些存在范畴(‘决定回到自己’、‘面对虚无站在自己之上’、‘愿意接受自己的命运’以及‘将自己交到自己手上’)充满力量地空转,过渡到德意志存在的普遍行动中,然后在政治的地板上加以摧毁。因此,如果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正好跟施米特提出的政治‘意志决定论’(Dezisionismus) 互相呼应——施米特把海德格尔的‘每个本有的此在’的‘能够完整存在’(das Ganzseinkönnen)转用到‘每个本有的国家’的‘极权整体’(Totalität)之上——那么这种呼应并非巧合。本有此在之自我主张对应于政治存在的自我主张,而‘死亡之自由’对应于在战争(作为严峻的政治情境)中的‘牺牲生命’。在这两种情况里,原则都是一致的,即‘事实性’。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当人把生命的‘内容’清除干净后,此生命所能剩下的东西。”(70页)哲学概念的深度没有改变,但是经过与施米特的政治意志决定论连接起来之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出口就逐渐呈现出来了。
在下一幕出场的就是1933年被选为弗赖堡大学校长的海德格尔。“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所有其他大学在这段关键的时间里,都缺乏一位不仅挂着纳粹党章,还能凭借学术成就而真能胜任此一职务的领导者。”(74页)在校长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题为《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Universität)演讲。洛维特对这次演讲的评价很精准、很深刻:“政变之后,思想被一体化了的教授们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小册子与演讲;跟这些比较起来,海德格尔的这场演讲具有很高的哲学性与深度,在措辞与构思上都算是小小的杰作。然而以严格的哲学标准来衡量,这篇演讲充满了模棱两可之处,因为在演讲中,海德格尔竟然有办法把存在主义本体论范畴的概念拿来为历史的‘此刻’(Augenblick,见《存在与时间》,第七十四节)服务,而且手法巧妙,使人产生某种印象,好像其哲学目的跟当前的政治局势先天就能够也必须合而为一,而学术研究的自由也同样先天能够也必须与国家的强制措施合为一谈。‘劳动服务’与‘兵役服务’被等同于‘知识服务’,以至于人们听完演讲后,不知道应该开始研究赫尔曼·第尔斯(Hermann Diels)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Vorsokraktiker),还是应该跟着冲锋队去游行。”(75页)因此他说既不能纯粹用政治眼光也不能完全从哲学角度来评价这一演讲,重要的是要看它所阐释的“大学的自我主张”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在演讲的开头就已经讲出来了:一方面反对国家侵害大学的独立性,强调大学的“自我主张”;另一方面又否定学术自由与学院自治的“自由”(liberal)形式,以便将学院无条件地纳入纳粹的“领导者”与“追随者”的框架里。洛维特说这是“一种奇特的矛盾”,其实我们知道一点也不矛盾,关键是对话语的解释权在谁的手里,既反对又否定与既要又要在修辞手法上也是一致的。海德格尔也解释了自己作为校长的义务既是在精神上领导全体教员与学生,同时又是被“人民交付的精神任务”所领导。这就是德意志的共同命运交付给大学和人民的任务,因此他号召学生作为一名意欲求知者(Wissenwollender),要“挺进”(vorrücke)到“最危险的岗位上”,要大步向前,下定决心承接德意志的命运——也就是要与元首与人民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看到和完全了解“这场崛起(Aufbruch)是多么壮观与伟大”。(77页)
洛维特还从话语措辞、语言风格上揭示了海德格尔哲学话语的真实要害:“纳粹式的政治论述与海德格尔哲学所使用的语言,两者都贯穿着暴力的表达方式。纳粹政治的独裁风格,与海德格尔激烈的、绝对化的措辞方式互相呼应。在两者所发出的挑战里,都有某种冒犯他人感受的阴险兴趣。只有程度的差异,方法却是一样的——最终都是‘命运’使一切意志得到合法性,并为其披上了一件历史哲学的外衣。”(79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接着还是语言的问题:德国的大学在被强制一体化之后,“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是在私人空间里的真实的语言,另一种是在公共领域里所说的虚假的语言——这种虚假的语言从四面八方将公共领域的一切组织给包围起来了。”(78页)在这种政治语境之中,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整套的此在概念(Daseinsbegriffe)便鲜明地显现出特定的德意志意义,并且在所有这些反复出现的语汇中传达出来:生存与坚决、存在与能在,“能在”与“本已”、“命运”和“必然”,在更常用的层面上就是规训、强制、艰苦、无可转圜、严苛、坚定、锐利、坚持、自立、投身、直面危险、变革、崛起、侵入……洛维特指出:“基本上所有上述的概念与语汇所表达的,是一个面对着虚无,而仍自我坚持着的意志所展现的痛苦而强硬的决心,是一个不与人和平、自己也不快乐的此在——它蔑视幸福与人性,并为此而感到骄傲。”(80页)洛维特说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1927年出版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书中的那个“本已的”和极端个体化死亡的概念在六年之后竟然可以如此改头换面,被拿来宣扬纳粹“英雄”的荣耀。1933年10月,纳粹德国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1月希特勒下令补办一场公民投票。海德格尔把弗赖堡大学的学生集合起来,以行军的队形带到投票所,让他们全体一起投下对希特勒决定的赞成票。他以校长身份发布的投票呼吁完全是纳粹风格的,同时也是海德格尔哲学里一个媚众取宠的例子。他呼吁“……元首给了人民一个最直接的机会来展现他最自由的决定:全体人民究竟想要本已的此在(sein eigenes Dasein),还是不想要。……元首之所以要求退出‘国际联盟’,不是因为虚荣心,也不是恋眷名望,不是盲目地刚愎自用,更不是追求暴力,而完全是因为他有清晰的意志,要无条件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去承受与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元首已经在全体人民的内心里彻底地唤醒了这意志 ,并将其凝聚为唯一的决心。在表明此意志的这一天,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83-84页)在这次投票呼吁的一周之前,海德格尔号召学生要以战斗的精神奉献自己,要坚信的法则就是相信元首:“元首本人,而且唯有元首本人,才是当今与未来德国的现实及其法则。”(86页)无论如何,作为德国的哲学家和大学校长而能够发出这样的号召,这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哲学家的洛维特深刻地指出:“海德格尔之所以追随纳粹的心态与思考方式具有实质上的原因,因此,若把他的政治选择单独拉出来批判或者美化,是不恰当的。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从他哲学的基本原则中寻求其政治选择的原因。”(88页)“海德格尔充满哲学意味的政治活动能到达什么程度,并不取决于某种意外的、让人惋惜的偏离正轨,而是源自他对‘存在’的理解的思想原则,在这样的思想原则里,“时代的精神”是具有双重意涵的。”(89页)法国当代哲学家菲利普·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1940-2007)在他的《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刘汉全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 2月)中也明确表示必须“因为海德格尔的政治态度”而对其思想保持“无限的怀疑”;同样曾是海德格尔学生的维克托·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在他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时事出版社,郑永慧等译,2000年12月)中从海德格尔一生的各个时期寻找其思想根源,证明海德格尔之追随纳粹并非一时的投机,而是他毕生的信念。其实,自从海德格尔的日记《黑皮书》于2014年初出版以后,这个问题本身已无悬念,海德格尔自己在日记中明确表达出其反犹主义与纳粹立场与他的哲学思想是不可分割的。
这就是在历史反光镜中映照出来的纳粹帝国统治下的哲学家形象。